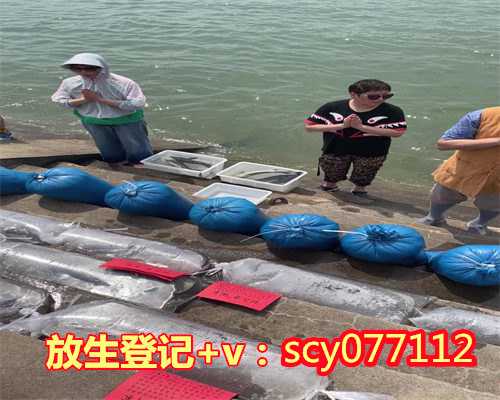上海,水库可以代放生吗,野生甲鱼放生好还是吃好
从中国古代文人士子文化心态积淀变化的历程来看,“自由”之具有纯粹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实乃始于佛教精神深深浸润过的魏晋士文化。有一个事实也许很能说明问题:给唐以来的中...
【上海凉水河放生群】「塘沽哪里适合放生」「菜市场买鸽子想放生」提供放生、全国代放生服务
佛教心性理论与审美主体的自由意识
佛教是追求自由弘扬自由的
海里放生一般放什么鱼
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由之于美,犹如空气、阳光、水之于生命。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审美创造的繁荣与否和成就高下都是取决于审美精神的自由程度,“美之花”只能在自由的精神土壤上盛开。魏晋时期,佛教心性理论激活了中土文人士子的文化心态中富于审美—艺术创造性的自由意识。这是魏晋时期思想活跃的标志,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精神转型的重要表征。
道教放生流程诚然,佛门戒律繁苛,似乎极大地束缚了人的自由,但这种束缚只表现于物态化的生活范畴。而在心灵、人格,也即精神生活上,佛教是追求自由、弘扬自由的。西哲有言:即使被关在“果壳”(一译“栗子壳”)里尚能自命为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这话形象地表明:即使物质生活窘迫到极点,只要有精神上的自由,就是君临天下的帝王,而且这种自由是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剥夺的。
在家居士放生仪轨可以说,佛教正是这样看待“物质”与“精神”之关系的极端地约束物质生活而极力给精神生活开拓自由。因而在佛门中,与浩如烟海的律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浩如烟海的关于心性理论的发明。华严五祖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说:“一藏经论义理,只是说心。”大智度论卷二十九称:“三界所有,皆心所作。”大乘起信论中也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而慧能禅宗和一部坛经更几乎将“佛法”等同于“心法”了。法国作家雨果说:比陆地更大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心。佛门所云之“心”,正可堪与之一比。对心之大及其无微不至、无远弗届之功用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对精神自由的强调。佛教是一种力图使精神自由获得纯粹独立意义的宗教。
放生乌龟的功德利益佛教大力弘扬的心性理论,使魏晋文人树立了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即:心灵自由,精神自由,乃是人生意义之真谛。与中国本土文化中生成的自由观比较,这种由佛教心性理论激活的自由意识表现出这样的特点:认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自由观,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实用与功利的羁绊。
放生螺蛳的害处老庄讲自由讲得最多,但庄子中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和解牛游刃有余的庖丁那种自由,骨子里其实还是有着很深的关乎事功名利的欲求,这种自由并没有同时既游心于世外,又游心于身外,仍须附丽于他事他物。故而学界有人认为,庄子的“回归自然”这个“回归自然”的要旨显然就是追求精神自由“有与官场闹脾气或对官场失望看穿的原因在里面”,也即“事功不遂”的逆反表现,这是中肯之见。
从中国古代文人士子文化心态积淀变化的历程来看,“自由”之具有纯粹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实乃始于佛教精神深深浸润过的魏晋士文化。有一个事实也许很能说明问题:给唐以来的中国士大夫开拓出极大自由度,并且几乎成为中国文人立身处世之要诀的“穷达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实为魏晋间接受佛教心性理论的影响而形成并巩固起来的。
先秦至两汉间的士人,基本上没有群落性的视个体精神自由为高尚价值的“穷则独善”观念,从伯夷、叔齐到孔子、屈原、司马迁,都只有“居庙堂之高”时才感到自由,一旦“处江湖之远”,便显出狼狈、困窘,甚至悲愤、绝望之态。这正如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描述的:“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因“不遇”,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都发出“我们到哪里去啊”的哀叹,三闾大夫屈原也在离骚中大放悲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直到魏晋时期,经过了以自由意识为核心内容,以名士高僧为最佳典范的“魏晋风度”的洗礼,士大夫阶层中才产生了其实颇具自我保护功能和自我确认意义的“穷则独善”思想,从而使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苏轼、范仲淹、王安石??等往返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文人士子既产生了“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也获得了实为“进亦乐,退亦乐”的精神自由。这种豁达的心态,最早是明显表现在陶渊明那里,他坦称:“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感士不遇赋)独善还是兼济,隐居还是出仕,蛰伏还是显达,都无所谓是非高下的区别,都是令人傲然自得、称心适意的事情。很多人认为,屈原与陶潜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范型。作为范型,二者的根本区别不是在于有没有渴望建功立业的“兼济”之志,而是在于有没有那份往往体现为着意开拓审美化人生的“穷则独善”之精神自由,而且这里的独善,真正是不需要任何功利性凭借的。
这种无须附丽于外在名利事功的自由精神,其形成,从根本上说正是得益于佛教心性理论。弘明集卷十一载何尚之答宋明帝问时说:“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这里说的六经典文本在济俗,就是指出了先秦两汉间的文化经典注重事功名利的本质特征;而求性灵真奥必以佛经为指南,则显然是说欲求真正的精神自由以及形而上的真理,须靠佛经引导。有论者指出:“在中国文化里,跟自由主义能发生亲和作用的是佛老思想。”
这里连带提到了老庄,但老庄的自由,如前所论,或者是能游心于世外却不能游心于身外,或者是能游心于身外却不能游心于世外,与身家性命和世俗欲求实际上还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后来道教希图羽化而登仙,极力追求物化形态的生命欲望的满足实不能完全说成是对老庄思想的背离。另外,从语源上来说,“自由”这个概念最早也是见于佛教经典,如坛经·般若品中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五灯会元中还记载了百丈怀海师徒讨论“如何是自由分”的问题。这一情况虽然出现在魏晋以后,但思想渊源由来有自。因此种种,说佛教心性理论对于激活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中最纯粹的自由意识发挥了大功用,应该是不为过的。
由于“自由”具有了目的论和价值论上的肯定性意义,故而魏晋时期的名士高僧皆以自由相尚。支道林“任心独往,风期高亮”,“绥心神道,抗志无为”,作逍遥论提倡忘怀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达人”、“至人”风范;特立独行的维摩诘被视为精神绝对自由的典型,成了游心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士大夫心仪神会的对象;东晋南方僧团领袖慧远大力标举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堪称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罕见的以无视封建王权为基本内容的自由宣言。这些模范影响之所及,遍于僧俗两界。
自由意识的崛起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发展嬗变意义深远。如果说周季学在官府制度的解体和百家争鸣的局面造就了一个士的阶层,那么,魏晋时期由佛教激活的自由意识则在士阶层中陶冶出了一批审美创造的精英。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等专门的文论、诗学著作和体大思精的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提出了诸如“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等致力于开拓无限的审美自由度的主张。也正是在此时,中国文化史上才出现了第一批真正完全摆脱了政教伦理的桎梏和事功名利的羁绊,不热衷于“学而优则仕”之追求,或虽然身居庙堂却游心于方外的具有独立纯粹品格的文人,如陶渊明、谢灵运、王羲之、孙绰、宗炳、支遁、慧远等名士高僧。
宗炳在其著名的指点“山水”的论艺文字中提出“畅神”说:“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孙绰在其喻道论中呼吁摆脱“世教”束缚,追求“方外”至真:“缠束世教之内,肆观周、孔之迹??焉复睹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陶渊明歌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诗二十首),都表现出一种以自由为天地间之大美的情怀。特别是宗炳的“畅神”说“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更明白宣示这种“大美”乃是其全部关怀和终极关怀之所在。据宋书·隐逸传载,宗炳“好山水,爱远游”,晚年犹叹“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这个“神游山水”说,极其生动地揭橥了“魏晋风度”中着力开拓审美化人生的自由精神。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里除了指出魏晋时代在中国美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之外,还阐明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一个命题:美是自由的象征“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加上“智慧”和“热情”,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学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完整意义的美学”,正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

从审美创造活动中主体方面的作用来看,魏晋美学之所以被认为是“完整意义的美学”之嚆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佛教心性理论激活了审美主体的自由创造精神。同时,也正是由于极大地开拓了主体精神上的自由度,才使得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子在“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也即在儒、道两家指引的人生价值观都无由实现的时代,另辟蹊径,亲近释门,抛弃名教物欲,转而到审美化的活动中去寻求人生价值,并使这种寻求得以实现成为可能。
塘沽哪里适合放生,菜市场买鸽子想放生,野生甲鱼放生好还是吃好